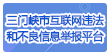本报记者 李建勇

两年前的金秋时节,“中国科幻文学40年高峰研讨会”在山西省阳泉市召开,作为研讨会应邀嘉宾,记者曾以“本土作家”身份作过《天上掉下个刘慈欣》的即席发言。的确,2015年以来的刘慈欣,称得上“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带到了世界科幻文学的前沿。两年后的秋天——8月29日,记者再赴阳泉,与刘慈欣就科幻文学这个话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充满未来感的国家
记者:首先感谢慈欣为我报近期创办的《孺子牛》副刊创刊号,提供了一篇很棒的文章《新冠疫情与外星人》!这篇文章与你素来关心的环境、生态、科技伦理、外星文明遭遇等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巨大挑战的提示,以及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记得2018年10月在阳泉召开的“中国科幻文学40年高峰研讨会”上你曾讲过,以前你去美国,跟美国人谈起中国的科幻小说,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有科幻小说?但是现在,中国科幻小说在欧美世界已经引起相当多的关注。听说近来日本也掀起一股“刘慈欣热”,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请你概括地介绍一下。
刘慈欣:中国的科幻小说输出到国外,也就是2015年以后的事吧。主要输出到英语世界——美国,还有一部分输出到欧洲。比较成功的就是《三体》的输出,目前它在英语世界包括美国、英国,还有一些英联邦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销量还是很大的,电子书和纸质书总量超过200万部。这种销量,即使与美国的科幻小说销量相比,也是很庞大的。《三体》(第二部)上过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输出销量最大的一部书。在英语世界之外的其他语种——大概有二十多个吧,德语版销售比较好,德国的科幻小说传统比较长一些;法语版销售也不错;俄罗斯也有一定的读者;在所有外语版中销售得最好的是波兰,按照人口比例销量相当高——平均130个波兰人中就有1个人购买《三体》,因为波兰的科幻小说也是有传统的,出过一个世界级科幻大师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一位杰出的作家可以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最近《三体》在日本的销售也不错,日本现在只出到第二部,一直处于销售之中,具体销量还不确定。这就是目前科幻小说输出的一个大致情况吧。销售好的也就是《三体》这一部书,其他的不行。我的其他作品也远远达不到这样一个程度。
记者:记得那次会上,谈到科幻在现实中的意义是什么?你说曾经认识一个外国学者说过一句让你很吃惊的话。他说,“你们这一代‘60后’的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人。”他补充说,“人类文明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代人像你们一样,从小到大经历过世界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很认同他的观点。当时你还说:“中国的未来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都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每个人都向往这种未来。”为什么?
刘慈欣:首先从外部世界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们经历了一两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们发展到现在好像开始有些失去活力。虽然它们现在仍然在各个方面占据着整个人类世界最前沿、最先进、最顶峰的优越态势,但是目前来看,它们的发展速度渐渐地变缓了,而且越来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一些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快速发展,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正是这种快速发展,使我们国家各方面的状况,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亲历者,感同身受,不用多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充满未来感的国家。“未来”这个概念——以前在中华文化的潜意识中似乎并没有“未来”这个概念,它的潜意识中觉得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也一样,之所以有变化,也只是朝代变了,皇帝换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但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所以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未来感”几乎是没有的。我查了一下,“未来”在中国的古代典籍里,出现得最多的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在佛经里出现最多……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中吸收了佛经里的很多东西,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引进的佛典中即有“去今来”,讲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中华传统文化向来珍视未来,尽管在字面上体现得并不多。比如“横渠四句”中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包蕴着宏阔深远的“未来感”……
刘慈欣:其实中华文化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未来感,但是是很淡的。那么到现在,第一次“充满了”未来感,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急剧变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未来感觉。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未来,包括世界的未来,对人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大前提下,科幻小说在中国开始受到注意,也开始繁荣,这是顺理成章的。然而,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未来和我们想象得并不一样,它不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排列出来,展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好的、不好的、最坏的,等等。未来不是线性的,是曲线发展的,我们很难去准确地预言未来,而科幻小说可能让我们对未来做好思想准备。这也正是科幻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是什么——在想象世界中展现宇宙的科学美
记者:《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辑姚海军先生,把你的科幻小说概括为“新时代硬科幻的美学标准”,就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那种创作类型。你在谈到自己的科幻文学创作理念时也说,你要在想象世界中展现宇宙的科学美。事实上,你的科幻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特征——换言之,你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宇宙级别的惊人事件,其中充满令人目眩神迷的超级技术;你以开创性的中国人的想象和视角,来描摹和透视宇宙空间的复杂未来。我记得你还讲过,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它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一种什么形态?或者说是怎样的一种趋势?
刘慈欣:说中国科幻文学处于初级阶段,首先是中国科幻小说虽然从很边缘的位置,到了今天吸引大众关注的位置,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科幻文学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比如,它的作家群人数很少,目前有一定影响力、经常有作品发表的,也就二三十人(也有人说四五十人)。这个与你知道的中国作协上万名会员相比,当然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再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3000多名作家参加,写科幻的就我一个人。另外,受众群体即读者数量也不多。我们不能只看《三体》,《三体》的确在国内的正版销量已经过千万册,数量相当庞大,但它只是一个特例。其他每年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市场销量情况都很一般。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科幻文学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家,也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到目前为止,真正有影响力的也就一部《三体》,包括我的其他作品也没什么影响力。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科幻文学只是一个起步状态、初级规模。我们跟美国的科幻作品规模比较一下,即可以看出差距。中国每年新出版的原创长篇科幻小说大致有几十本不到一百本的样子,美国每年新出版的原创长篇科幻小说大概是2000本;中国的科幻作家群体大约是二三十人,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的会员即有3000多人,这就是差距。另外还有科幻电影上的差距,美国的科幻电影几乎全面占领了全球的科幻电影市场,占据全球科幻电影票房的百分之六七十。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也是在国内影响力巨大,在国外并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说,中国的科幻文学包括文化市场,总的来说只处于一个起步状态。但是,中国的科幻文学前景是十分光明的,因为我们有目前这个大环境,面临着一个大时代。美国的科幻作品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发展起来的,那个时期是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那个时期,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在快速发展。其实中国现在很像当年美国的状况,处于起飞状态、快速发展状态。如果这个态势能够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在大概念意义上的科幻,应该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因为我的《三体》这本书十分成功,受到广泛关注,将来等它的电影和电视剧拍出来,还会继续受到高度关注;但是,《三体》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科幻还比较落后、比较初级、规模很小的现实状况。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看到。
记者:《三体》获得“雨果奖”后,阳泉,包括你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娘子关,已然成为很多科幻读者心中向往的地方。你的几部小说比如《地火》明显带有“文学与故乡”的题材和内容。“文学的故乡”阳泉或者说娘子关,对你的科幻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刘慈欣:准确来说,我在阳泉生活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娘子关生活和工作,它和阳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的人生,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等等,对其作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另一方面,科幻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又是不一样的,它是描写超现实的、远离现实生活的一些东西。从这一点来说,科幻作家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作品的影响要小一些;即便有影响,也是通过一种很曲折的渠道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至于怎么展现,连作者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对科幻作家影响最大的现实是大环境——即整个人类世界未来变化发展的趋势。尽管中国科幻小说包括我自己的小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现实的,但这只是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也仅仅是一个背景、一个想象力起飞的平台,它并不是作品的主要部分。我是从一个科幻读者、科幻迷,成为一个科幻作家的。用科幻小说来反映现实,隐喻现实,批判现实,对我来说并不是主要目的。我创作的最主要目的,是去想象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的一些东西,能够让读者从很疲惫的现实生活中,看得更辽远一些,视野更广阔一些,思考更深邃一些。
记者:科幻小说中既有“科”的元素,亦有“幻”的成分。你的科幻小说中有许多对形而上的宇宙观之呈现。请谈谈你的宇宙观与宗教信仰、“自然神”以及老子所讲的“道”,有着怎样的区分与联系?
刘慈欣:科幻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有着浓重的西方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背景,但是科幻文学最主要还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我是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的小说里面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东西,主要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至于宗教以及形而上的东西,在科幻小说里也是经常出现的重要元素。很多科幻小说描写到最终极的哲学层面的宇宙状态、时间和空间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有的是无神论思维,有的则带有一定宗教色彩。从我自己来说,只是在尽力描写宇宙的那种宏大,那种神秘,那种广阔,以及宏大的宇宙与渺小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与宗教无关。至于你所说的老子的“道”,属于中华传统文化范畴。坦率地讲,我不太了解古老深邃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到现在也很难说清老子的“道”到底是什么。然而,宗教和宗教感情应该区分开来,一个人可能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很可能会有宗教感情。当仰望星空看宇宙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会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这就是一种宗教感情吧?这种感情在我的科幻小说中很常见。面对宇宙的宏大和人的渺小,人之所以情不自禁产生的这种空间与时间上的渺小感,以及对宏大宇宙的敬畏感,是所有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个精神基础。这也就是你前面所提到过的,我的科幻小说创作理念,是尽可能在想象世界中展现宇宙的科学美。
怎么办——让科幻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记者:爱因斯坦讲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科幻文学创作的全部精髓在于想象力。而现在科幻小说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所依赖的科学的神奇感在逐渐减退。这就更需要发挥奇妙的想象力。对你而言,如何来重建神奇感?怎么去激发想象力?
刘慈欣:科幻文学本来就是建立在对科学的那种神奇感之上的。它的黄金时代就是上世纪早期及中叶,科学技术正在显示出那种改变生活的力量,但同时还没有充分地渗透到生活中的那么一个时段,科学具有非常美妙的神奇感,科学带来的未来也令人向往。正是在这个时代,科幻小说迅猛发展起来。但是,今天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失去它的神奇感。失去神奇感,对于科幻小说来说——你注意我下面这句话——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是致命的!科幻小说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衰落,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你问到怎么办?怎么来重建这种神奇感?我说句坦率的话,没办法!因为外国的、中国的科幻作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一个努力就是想把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用于科幻小说创作之中,让科幻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在科幻文学史上,称作“新浪潮运动”。现在看来这个运动并不成功。而今很多美国科幻作家和我们中国的一些科幻作家,把科幻作为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一个独特的角度,试图从这方面来挽救科幻。但是目前看来也不太成功。美国的科幻作家越来越关注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更多地关注种族歧视、种族压迫、性别歧视以及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但是总的看来也不成功,让人感到美国科幻文学一天一天地失去活力。现在整个世界范围的科幻文学都处于衰落状态。我觉得这很正常。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它诞生的时刻,有它处于旺盛发展的时期,当然也有它衰落的时期,甚至还有它的终点。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至少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一段时间里,科幻文学还是有着很大发展空间的。这是由中国科技当下乃至未来的迅速发展、渐次壮大的大环境和大趋势所决定的。
记者:由于《三体》的巨大成功,太耀眼、太震撼了!作为科幻文学史上里程碑之作,《三体》发表到现在已过十来个年头。如何超越自己?对你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下一步有何创作打算?
刘慈欣:正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科幻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衰落是大势所趋,这不是哪一个人能改变的。首先,因为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没办法再提供科幻小说所必备的——一种叫神奇感,一种叫疏离感。其次,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特别是像科幻这种大众文学作品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外部因素。比如《三体》的成功,首先是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质量,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乃至运气。但是机遇这东西,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左右的。你不能说我再写一部作品,还会碰到那么好的机遇,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变了。现在的读者五年就是一代人,他的欣赏取向五年就会大变一次。我当然想超越《三体》,但我并不奢望下一部作品还有那么好的机遇。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创作的动力、创作的兴奋感,然后写出一部自己觉得很震撼、很满意的科幻小说。这是我现在每天都在努力的方向。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一方面期待科幻文学在提升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国家创新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似乎公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科幻文学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乃至它独有的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对此你怎么看?
刘慈欣:科幻小说首先是一个文学体裁,而且是一个大众文学体裁。这一点必须明确。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和障碍之一,就是把科幻过分工具化。比如晚清时期,科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就被工具化。作为晚清知识分子像梁启超等人,即把科幻文学作为他们渴望中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一个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大致是从鲁迅先生开始吧,又把科幻作为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一个工具。鲁迅曾大力倡导过中国的科幻小说,他亲自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寄希望于用科幻小说在大众中普及科学与科学精神。鲁迅小说代表作品之一的《狂人日记》,其实我现在想想,就很像科幻小说。但是,科幻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毋庸讳言,历史上将科幻文学不断工具化,其实阻碍了科幻文学的发展。在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谈论科幻文学的健康发展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文学本身是有使命的。但科幻文学首先得“好看”,它需要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需要有覆盖面很广的读者,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所以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去潜心创作能够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的优秀的科幻作品。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文学体裁,它确实能够开阔读者的想象力,启发读者的创造精神,活跃人们的创新思维——特别是对青少年而言。从这一点来讲,科幻文学确实能够对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从更广义的方面来看,科幻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和商业符号,它在当今及未来中国的大环境中,将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我们的思想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创作去迎接未来。(画像作者罗雪村)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9.21)


 豫公网安备41120202000222号
豫公网安备41120202000222号